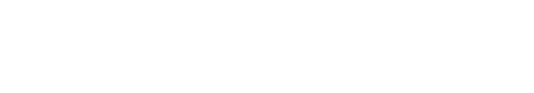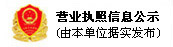饺子印象
儿时,最盼过年,因为只有过年,才能吃到一顿饺子。在大年夜,年炮放过,黄表纸烧过,白生生的饺子端上来。我用筷子夹起饺子,往滴过香油的醋碗里一蘸,往嘴里一填,用牙齿一嚼,那才叫“过隐”哩!最爱吃饺子的,要数妹妹红儿,红儿嘴馋,我常拿她逗乐:“小饺子儿,冒热气儿,流酸水儿”。我这么一说,果然奏效,红儿吧哒吧哒嘴儿,不一会儿竟流出酸水来。
让人忘不掉的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,那年的饺子,让我终生享用。那是我结婚后的头一年,我家添了玉儿,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有了嫂子。玉儿可是包饺子的“行家”,无论是“擀皮儿”,还是“夹馅儿”,堪称绝活儿。那时,参与包饺子的,只有玉儿和母亲,我笨手笨脚,只有吃的份儿,弟弟管着放年炮,饺子还没包好,一挂年炮早早地拴好了,只等着放。那时放年炮不像现在这么大方,饺子没煮熟,只能从成挂的上面拆下来,零星地放,等煮熟了饺子,才成挂地放。那时,父亲还健在,他乐得像个孩子,躺在炕上,拉一阵子“二胡”,就窜到院子里,“咚”地放它一炮,这一“咚”可不要紧,屋顶上的灰尘“唏哩哗啦”。
要说包饺子那场面,蛮有趣的。母亲和玉儿,坐在火热的炕头上,一边拉呱儿,一边包年饺,不一会儿,盖垫落满一大片。玉儿手巧,时不时地包出花样,忽儿包出个小巧玲珑的“花苞”,忽儿捏出只灵气活鲜的小鸟儿,吃到“花苞”将来要娶个好媳妇,生个白胖小子,当然这是她对弟弟说的;谁能吃到“小鸟”,谁就能择佳偶,飞高枝,一辈子不愁吃,不愁穿,风风光光,富丽堂皇,这是她对俩妹妹说的。
那时,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刚刮到村子,想“冒富”“暴富”的心理儿刚冒芽儿,就是水面上冒出个“大鲤鱼”,兴许没人敢捞捞试试。人们都忘不了,在那六七十年代,人们有话不敢说,生怕揪尾巴,上台子,挨批斗。那时我还年轻,刚好二十来岁儿,想当个“诗人”或“作家”什么的。包年饺的事儿在脑海里沉淀久了,就想着把它写出来。那是81年冬,快过年的时候,我把包年饺的事写成了诗,交给文友曹成章老师看,曹老师看过后,风趣地说:“年饺没熟哩,还得焖焖”。于是,我又改了七八遍,直到满意才寄给报社,没想很快有了回音,我的处女作《包年饺》在省报《农村大众》“沃土”副刊上发表了,诗是这样写的:“炕头上的娘和嫂/啦着呱儿包年饺/新呱挤满心窝窝/出口就是喜春调//娘啦‘富’字红花开,捏个花儿正绽苞;嫂啦如今‘农家乐’,扭个鸟儿喳喳叫。//娘俩啦得兴味儿浓,弟弟挑起一串炮,竹竿顶上金星爆,农家笑声又点着……”
十里看花
我说的“花”,可不是花园里展放馨香的“花”,而是节日里的礼花。元宵节是绽放礼花的大好时节。八年前,我还在乡下住,家有点儿偏僻,可偏僻自然有偏僻的好处,元宵夜,溜出家门,不费多少腿劲儿,就能赏到焰火。你瞧,在那紫色的星空下,那五颜六色,忽隐忽现的焰火有多好看。因我是在十里之外看“花”呢,所以只感到好看,却听不见声音,那剩余的部分,自然要靠想象去补偿了。
我想那“着了彩”的夜空,定然是世界上最美的花园;我想在那美丽的花园儿里,定然有美丽的奇十里看花葩绽开奇花异朵;我想那朵儿下面,定然有无数张脸儿,定然被映成桔红、紫红、橙黄……。多美的小城的夜景啊,让那一张张脸儿、一颗颗心儿分享盛开,分享灿烂。我羡慕焰火,羡慕她的丰姿绰约,羡慕她的璀璨奔放。我更艳羡那燃放焰火的人,他们点燃着激情,放飞着自由,放飞着快乐,他们,定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!我情不自禁地想,一朵焰火,能抵得上多少根“滴滴金”呀!从前,家庭穷困,买不起年炮,就到处捡拾“哑炮”;买不起礼花,就燃放“滴滴金”。后来,索性连“哑炮”不捡了,“滴滴金”也不买了,而是用最廉价、最贪婪的方法:张开耳朵,到处搜集年炮的炸响;睁大眼睛,到处捕捉礼花的色彩。
记得那年元宵节,为了看礼花,我蹬着“大金鹿”,载着孩子他妈,往返二十里路,专程去十里看花辛店看焰火。嘿,那焰火场面真够大的,黑压压的人群,流光溢彩的世界。你往高处瞧,那被燃着的焰火,像一颗曳光弹,又像一颗夜明珠,一个追着一个,“嗖”地一声打上夜空,然后“嘭”地一声炸开,霎时间,半空里华彩尽绽,像孔雀开屏,像天女散花,像金菊怒放,像银瀑吐珠…………,这么好看的景致,这么盛大的奇观,“妖术”似的,吸着我的脚步,勾着我的眼睛,让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前移,让我的眼睛淌出泪来,直到有点晕弦的眼睛落上一滴粉尘,方才从梦的世界里醒过神儿来。听人说,这是临淄区委、区政府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焰火晚会。这些年,临淄区经济社会,就像那节日的礼花,步步高升,步步登彩。扬中华大业,振临淄雄威,临淄夜空的焰火一年一个新花样,一年十里看花一个新景观,让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
好像我与焰火有缘似的,自从步入那闪光的21世纪,我就搬到了辛店城区,住上了高楼,再用不着十里之外看花了。可连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,日子好了,赏焰火的欲望反倒淡了起来。当我想起“距离产生美”的雅句时,竟禁不住地要到乡下去,再来它个“十里看花”,说不定会把“滴滴金”与小城的焰火联系起来,构成一个彩色的金色的立体世界!
燃放“滴滴金”的年月
“滴滴金”,也有人称它“滴答金”,因燃放时从芯子里滴出金色的火花而得名。“滴滴金”这个受孩子燃放“滴滴金”的年月们喜爱的年节礼物,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最为常见,如今随着小日子芝麻开花,“滴滴金”差不多要销声匿迹了。
要寻觅“滴滴金”,还须乘着时光的倒行船儿,追溯那贫困潦倒的年月。在那年月里,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,每天只知道玩玩玩,乐乐乐,不知道“愁”为何物,更不思“为三斗小米而折腰”了,只知道外面有个大世界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那时,家贫得叮当响,过大年,我们兄弟几个常常钻在柴禾堆里,敲打着破盖垫儿当鞭炮;过元宵节,就到商贩那里丢几个“钢崩儿”,换回一把“滴滴金”,等到天黑时燃放。
说起“滴滴金”,大约有圆珠笔芯那么长,用毛草纸卷的,里面盛着的黑黑的药,是木碳碾碎后制成的,其工艺就跟乡下人卷“蛤蟆烟”差不多。它一端的药粉大概是蘸了胶,就像给药粉加了个“档板”,不到点火时分,它决不“外逃”;另一端为了防止药粉“撒野”,早就用草纸打成个“结儿”,像个小尾巴似的,这意味着“滴滴金”亮了“黄牌”,意思是:要守住寂寞,不到出手时,万不能出手。其实,那些药粉只是火花的种子,它也有酝酿期和生长期,这酝酿期和生长期,都掌握在主人手里。你燃放它时,不必提心吊胆儿,更不必倒抽冷气,你只要走到个避风的地方,用燃着的火柴梗朝着有药的一头儿只一蹭,那药就心有灵犀,丝丝缕缕地冒出细烟,这些烟缕晚间是看不到的,耸耸鼻孔可以闻到。“滴滴金”燃着后,你像倒提黄鼠狼那样,捏住它的“小尾巴”,你就可以尽情地享受“火花”了。假若你嫌“滴滴金”形影单只,冒出的火花单调,还可成把地燃放,不过那太有点儿“奢侈”了。你要显示“大气”,你的动作可大方点儿。你提着“滴滴金”,或走,或疯跑,或边疯跑边摇,都由着你呢,但你不必大叫,——你此刻的心情,早就被火花说出,你就觉得,你不是提着“滴滴金”,而是提着一束“倒挂金钟”,让夜色遍生灿烂!
我爱“滴滴金”,爱它的小,爱它从小小的躯体里发出的风儿扑不灭的光焰!“滴滴金”,它不像性格暴躁的鞭炮,动不动就暴跳如雷,也不像性情鲁莽的礼花,动不动就怒气冲天。“滴滴金”,它就像大草原上的羔羊,性情温顺;它就像农家院里的枣花,谦卑恭让;它就像大地上的苗儿,给点儿阳光就葱翠,“滴滴金”,它是多么容易满足呀,给点儿火儿就生出火花儿,洋洋洒洒,向世界发表金色的宣言!
在我们家乡,元宵节也算个了不起的大节,从正月十四挑灯,到正月十六收尾,锣鼓不断,鞭炮不断,焰火不断,燃放“滴滴金”自然也是。元宵节一到,伙伴们都“火”了,不过不是生气,而是忙着给天空“弄彩”呢!只是伙伴们花天喜地、神气活现地挑着五颜六色的灯笼,并不引我羡慕。——他们有他们的彩色的梦,我有我的金色世界!尽管,“滴滴金”,不像大礼花、二礼花和雷子那样大鸣大放,可我还是相信它是有色彩、有声音的。尤其在那被银星或礼花装点的夜色里,你怀着一种心情静听,“窸窸簌簌”,“窸窸簌簌”,是“滴滴金”在“开花”呢!我们这群“穷光蛋”,不!我们这群快乐的 “小天使”、“小皇后”早就醉在那里,醉在那暗淡的光影里,任凭母亲猫儿般地呼叫,我们却像没长耳朵似的。
只是在那燃放“滴滴金”的年月里,燃放“滴滴金”的为数不多,多了,我们就组成“‘滴滴金’燃放队”,与奔跑着的时光一起,组合成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可叹韶华易逝,梦不复来。假若梦能成真,我倒要真的把那燃放着金色火花的“滴滴金”,从闪光的记忆里取出来,捧给那些吃肯德基、玩电子游戏和看卡通片的孩子们,告诉他们,在那过去的苦难的岁月里,也曾藏着个美好的乐园。
作者:刘建博:中国诗歌学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诗集《黑岩石》《天蛇》。

作者近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