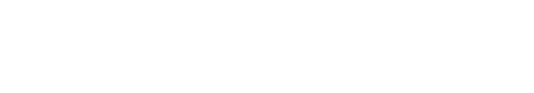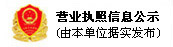临淄民俗-----春耕情景图
日期:2016-01-18 21:02:14 发布 浏览次数:4345
按:临淄民俗学家王毅先生在最近出版的《临淄古今民俗》书中,用生动、形象的文学笔法对临淄传统的民俗民风做了描述,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幅乡村美景画卷。这里我们选择了其中一篇给大家共赏。
旧时,清明过后,气温升高,桃李花开,蜂蝶飞舞,香椿萌嫩芽,榆钱圆又嫩,梁燕正衔泥,鹊巢已双栖,正是春耕时节。
春耕最重要的准备就是“搭犋”。《辞典》对“犋”的解释为“牵引犁、耙等农具的畜力 单位,能拉动一种农具的畜力叫—犋,有时是一头牲口,有时是两头或两头以上。”临淄大多数土地粘、硬,没有一头牲口的“犋”,都是两头以上。村里一户农民能喂养两头牲畜毕竟是少数,除非是几户大财主不须要联户搭犋,绝大多数农户在春耕前都要各自寻求适合的农户插夥搭犋。有的两骡搭犋,有的两牛搭犋,有的牛驴搭犋,称之为“二杆子犋”;有的两牛一驴搭犋,有的一牛一骡一驴搭犋,有的两骡一驴搭犋,称之为“三杆子犋”;有的四头毛驴搭犋,称之为“四驴子犋”。邻里乡亲这种自愿插伙搭犋耕地形式,是自古传承下来,代代相传,它昭示着自然小农经济互助合作的旺盛生命力,也反映了民间自发群体的凝聚力。关于“搭犋”而引发出来的俗语颇多。如,几个人伙夥干某一件事,不能协力同心,使不齐劲,为首掌握者既生气又棘手,称之为“四驴子犋扶梨匠——喊破嗓子活生气”。又如,某头头为集体办事踏踏实实,任劳任怨,带领大伙埋头苦干,称之为“领墒牛”。再又如,多人伙夥干某件事,某中有些人想另立炉灶,各干各的,管这种行为称之为“拆犋”。再又如,人们对连襟兄弟,称之为“一拉杆子”。这些以“搭犋”引发出来的俗语,既形象又贴切。
要耕地先让牲口上犋,也称“套犋”。用畜力牵引木犁、铁弓犁,耕地前先把套索在地上摆好。领垧牛是使役好的耕牛,套索放右边,左边是次等的牛或驴,两套索的后钩分别挂在二杆上,二杆中间的后钩挂在木犁上。(要是“三杆子犋”则挂在“三杆子”)上再把“甩绳”放好,就可以套牲口了。先套领墒牛,再套左边牛或驴(若驴可早戴上迎膀子)。用绳拴在牛鼻圈上(或牛左耳上),驴可用缰绳绕鼻梁一圈叫“打过梁”再接到甩绳上。两根甩绳栓在犁把上。扶犁人右手握犁把,左手拤腰,肩上背耕地大鞭,就扶犁耕田了。吆喝声和着鞭子声驱赶牲口加快行走。“哦,哦——”随着喊声,一扽一扽拉甩绳,牲口就知道略向右走;“咦、咦、咦——”牲口就略向左走;若喊“哦回——”就向右回头;若喊“咦回——”就向左回头走;若喊“驾”就是加快,某个牲口拉不平二牛杆就用鞭子打;若喊“唷——”,就是停下,使役好的牲口都懂得各种吆喝声。若出坡时,将犋套好后,把它挂在拖车上,再将耙和犁放在拖车上,便驱赶着一犋牲口来到地头。耕地匠须先看一看地块去年是“伏耕的”(从地块中间起耕)还是“绞耕的”(从地块两边起耕)从而决定今年与之相反而耕。如果是“绞耕”最后中间的“墒沟”较深,可“倒墒”一遭,以减轻平墒沟的麻烦。
如果是绞耕,插犁前,扶犁匠须查看“桑稞“。临淄有民俗:每块地的两头和中间都植有一丛桑稞。它是小农经济各地主户地边界的标志物,由双方共同植定,长期存活,长得过大时,须双方共修“桑稞”。耕地匠按桑稞为界而耕,避免了争地边的纠纷。
提到耕地的技术,有两则谚语,其一曰“耕地不用学,两眼瞅瞅前砣。”其二曰:“耕地深与浅,动动犁把‘两楔’见效验。”搭犋耕地是牲口的重活儿,累得骡驴出汗,牛卧墒沟。因此间歇时间较长,须得等到骡驴消汗,牛“嚼沫”之后为度。耕地匠们趁机凑成堆,打火抽旱烟,下“土棋”……
乡亲们搭犋耕地是一种纯朴的田园乐趣。秋天的早晨,田野里雾气濛濛,像挂在空中千万片待染的白纱,缓缓地摆动。“噢——嚎——”,“驾——吁——”这拖长的吆喝牲口的回声在雾霭里回荡;驱赶牲口的响鞭在空蒙中炸响。远眺,晨雾中一犋犋拉犁拖耙的剪影像耍皮影戏似的。近瞅,那骡马犋,长鬃劲蹄,喷鼻声伴随着“迎膀”有节奏的的摩擦声,唿唿行进,垡子如浪翻滚……扶犁匠右手扶着犁把儿,左手手腕顶在腰坎上,虎步生风,满怀的激越和豪气!双牛犋刚慢条斯理,稳扎稳打。扶犁匠悠然地踏着八字步,满脸的庄重、严肃。
俗说“扶犁先学鞭”。牛皮拖鞭,短柄,鞭身近丈长,近把儿处有馍馍般粗,递次渐细。有爱俏的人,鞭上系有节节红缨,挥动起来如赤练横空,煞是惹眼。因用右手扶犁把儿,挥鞭只能用左手,这更增加了学鞭的难度,刚学摔鞭时既不响,也没力度,还有“缠子辘轳头”的危险,扶犁匠摔的正鞭劲而直,犹如蛟龙打挺儿,抽回来的反鞭恰似长蛇摆尾,两鞭递响如霹雳轰鸣。扶犁匠打的鞭有两种:其一曰“实鞭”,既响且重,落在牲口脊背上顿时跳起指头般粗的鞭痕儿;落在骡马的脖颈上,鬃毛如用刀剪一般,纷纷扬扬。故而扶犁匠的拖鞭经常背在肩头上,不轻易放实鞭,只要用鞭把儿轻轻敲敲犁把儿,犋上的牲口就乖乖地卖劲,听使唤。其二曰“虚鞭”,它只有如雷的响声而不着牲口的皮肉,此鞭也叫响鞭。临淄的扶犁匠们有经常放响鞭的习惯,那是他们自我陶醉的一种乐趣罢了,并非为了打牲口,故家乡有“扶犁匠打响鞭——自图快活”的歇后语。踏耙更有趣。在刚耕过的面窝儿似的土地上,扶犁匠站在耙的踏板上,一手持住牲口缰绳,一手挥动着摇鞭,随着双脚交替起落,使耙均匀地摆动拖行。耙像一把巨型的梳子,划出几十条波浪线……耙过的地块犹如一架琴弦颤抖的巨型古琴……踏着耙在松软的地面上滑行,既有坐荡椅的飘荡感,又有坐雪橇的滑行感。耙坷垃地,耙上下颠簸,比坐花轿还惬意呢!
晚归时,幻变、神奇的犁铧更有趣。每当日薄西山,晚霞映天。老牛摔着尾巴慢悠悠地拉着拖车归来。扶犁匠轻哼着梆子腔,高了兴左右开弓,放几声响鞭,惊得停树待宿的鸟雀扑愣愣乱飞,引得光腚孩子雀跃拍手……拖车上那面擦拭得油光可鉴的犁铧上,映物照人,变幻莫测,它简直是一面小型的哈哈镜:它能把西山上高大的柏树照成矮矮的狼尾巴蒿;它能把山上低矮的小庙照成一把硕长的出鞘宝剑;它能把晚归的绵羊照成高大的骆驼;它能把清瘦的老扶犁匠照成笑眯眯的弭勒佛。光腚孩子们当看到他们的苹果脸照成“二指脸”小鬼时,闹罢恶作剧后,在路旁二指厚的簿土里打“旁连”、竖“直立”……
搭犋耕地虽说能自寻些田园乐趣,但更多的则是劳累和烦恼。用大骡大马搭犋的毕竟是少数,大多数农户是老牛、瘦驴搭犋。笔者十六岁时就曾当过老牛瘦驴犋的小扶犁匠。老牛在狭窄而暄松的墒沟里打别腿; 瘦驴的腿像抽筋,蹄子抬得老高落不下,其乏力之状不言而喻。笔者摔的鞭既不响又无力度,打老牛一鞭,腚一斜,打瘦驴一鞭,腰一弓,把犁拉得东倒西歪,笔者只得像醉汉逛街似的“救犁”,耕的地像长虫吃了蛤蟆。一天下来嗓子喊哑了,浑身像散了架,躺在土炕上“翻饼”……然而四驴子犋的扶犁匠却是最生气、最烦恼的差事,四个毛驴搭一犋,像一串乱蹦哒的蚂蚱,叫驴们拉犁虽无力而性欲却十分亢奋,发起性来,大叫不止,东咬一口,西踢一蹄。草驴们吓得不是畏缩不前,就是奋力挣脱。扶犁匠既使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。若狠打几鞭,打着的拉一膀,打不着的松一套,不是这个脱了“杆儿”,就是那具拌了腿,乱成一窝蜂似的。真是应了“四驴子犋活生气”的俗语。要说最苦最累莫过于冒雨踏耙,搭犋是几家畜力和农具的组合,确实不易,小风小雨,谁敢轻易歇犋,再加上“只耕不耙”是大忌,俗话“耕地不耙,炉碴,瓦垡”,因此不管耕了多少地必须赶在雨前耙完。当暴风雨初来时,还能拖泥条踏耙。待到暴雨倾盆而降时,就只能“畜拔响蹄”,人“跟耙踩藕”了。人畜成了落汤鸡,其苦累之状可想而知。
扶犁匠们尽管至苦至累,反而煅红了他们那颗爱犁、护犁的执著、赤诚的红心。俗说扶犁匠有两大怪:“鞋底完好帮早坏,蓑衣不披给犁盖”。凡是耕地回头、间歇,晚归“上拖”时,扶犁匠总是习惯地用右手提起犁,用左脚的鞋帮将犁铧擦拭几下,故而鞋帮先破。扶犁匠的蓑衣,即使雨下得再大自己也不披,宁愿自己挨淋,也要将犁铧盖个严,以防焐犁。扶犁匠们的敬业之心可见一斑。
春耕之后,为了保墒,间或再耙几次,就等雨后春播了。
旧时,清明过后,气温升高,桃李花开,蜂蝶飞舞,香椿萌嫩芽,榆钱圆又嫩,梁燕正衔泥,鹊巢已双栖,正是春耕时节。
春耕最重要的准备就是“搭犋”。《辞典》对“犋”的解释为“牵引犁、耙等农具的畜力 单位,能拉动一种农具的畜力叫—犋,有时是一头牲口,有时是两头或两头以上。”临淄大多数土地粘、硬,没有一头牲口的“犋”,都是两头以上。村里一户农民能喂养两头牲畜毕竟是少数,除非是几户大财主不须要联户搭犋,绝大多数农户在春耕前都要各自寻求适合的农户插夥搭犋。有的两骡搭犋,有的两牛搭犋,有的牛驴搭犋,称之为“二杆子犋”;有的两牛一驴搭犋,有的一牛一骡一驴搭犋,有的两骡一驴搭犋,称之为“三杆子犋”;有的四头毛驴搭犋,称之为“四驴子犋”。邻里乡亲这种自愿插伙搭犋耕地形式,是自古传承下来,代代相传,它昭示着自然小农经济互助合作的旺盛生命力,也反映了民间自发群体的凝聚力。关于“搭犋”而引发出来的俗语颇多。如,几个人伙夥干某一件事,不能协力同心,使不齐劲,为首掌握者既生气又棘手,称之为“四驴子犋扶梨匠——喊破嗓子活生气”。又如,某头头为集体办事踏踏实实,任劳任怨,带领大伙埋头苦干,称之为“领墒牛”。再又如,多人伙夥干某件事,某中有些人想另立炉灶,各干各的,管这种行为称之为“拆犋”。再又如,人们对连襟兄弟,称之为“一拉杆子”。这些以“搭犋”引发出来的俗语,既形象又贴切。
要耕地先让牲口上犋,也称“套犋”。用畜力牵引木犁、铁弓犁,耕地前先把套索在地上摆好。领垧牛是使役好的耕牛,套索放右边,左边是次等的牛或驴,两套索的后钩分别挂在二杆上,二杆中间的后钩挂在木犁上。(要是“三杆子犋”则挂在“三杆子”)上再把“甩绳”放好,就可以套牲口了。先套领墒牛,再套左边牛或驴(若驴可早戴上迎膀子)。用绳拴在牛鼻圈上(或牛左耳上),驴可用缰绳绕鼻梁一圈叫“打过梁”再接到甩绳上。两根甩绳栓在犁把上。扶犁人右手握犁把,左手拤腰,肩上背耕地大鞭,就扶犁耕田了。吆喝声和着鞭子声驱赶牲口加快行走。“哦,哦——”随着喊声,一扽一扽拉甩绳,牲口就知道略向右走;“咦、咦、咦——”牲口就略向左走;若喊“哦回——”就向右回头;若喊“咦回——”就向左回头走;若喊“驾”就是加快,某个牲口拉不平二牛杆就用鞭子打;若喊“唷——”,就是停下,使役好的牲口都懂得各种吆喝声。若出坡时,将犋套好后,把它挂在拖车上,再将耙和犁放在拖车上,便驱赶着一犋牲口来到地头。耕地匠须先看一看地块去年是“伏耕的”(从地块中间起耕)还是“绞耕的”(从地块两边起耕)从而决定今年与之相反而耕。如果是“绞耕”最后中间的“墒沟”较深,可“倒墒”一遭,以减轻平墒沟的麻烦。
如果是绞耕,插犁前,扶犁匠须查看“桑稞“。临淄有民俗:每块地的两头和中间都植有一丛桑稞。它是小农经济各地主户地边界的标志物,由双方共同植定,长期存活,长得过大时,须双方共修“桑稞”。耕地匠按桑稞为界而耕,避免了争地边的纠纷。
提到耕地的技术,有两则谚语,其一曰“耕地不用学,两眼瞅瞅前砣。”其二曰:“耕地深与浅,动动犁把‘两楔’见效验。”搭犋耕地是牲口的重活儿,累得骡驴出汗,牛卧墒沟。因此间歇时间较长,须得等到骡驴消汗,牛“嚼沫”之后为度。耕地匠们趁机凑成堆,打火抽旱烟,下“土棋”……
乡亲们搭犋耕地是一种纯朴的田园乐趣。秋天的早晨,田野里雾气濛濛,像挂在空中千万片待染的白纱,缓缓地摆动。“噢——嚎——”,“驾——吁——”这拖长的吆喝牲口的回声在雾霭里回荡;驱赶牲口的响鞭在空蒙中炸响。远眺,晨雾中一犋犋拉犁拖耙的剪影像耍皮影戏似的。近瞅,那骡马犋,长鬃劲蹄,喷鼻声伴随着“迎膀”有节奏的的摩擦声,唿唿行进,垡子如浪翻滚……扶犁匠右手扶着犁把儿,左手手腕顶在腰坎上,虎步生风,满怀的激越和豪气!双牛犋刚慢条斯理,稳扎稳打。扶犁匠悠然地踏着八字步,满脸的庄重、严肃。
俗说“扶犁先学鞭”。牛皮拖鞭,短柄,鞭身近丈长,近把儿处有馍馍般粗,递次渐细。有爱俏的人,鞭上系有节节红缨,挥动起来如赤练横空,煞是惹眼。因用右手扶犁把儿,挥鞭只能用左手,这更增加了学鞭的难度,刚学摔鞭时既不响,也没力度,还有“缠子辘轳头”的危险,扶犁匠摔的正鞭劲而直,犹如蛟龙打挺儿,抽回来的反鞭恰似长蛇摆尾,两鞭递响如霹雳轰鸣。扶犁匠打的鞭有两种:其一曰“实鞭”,既响且重,落在牲口脊背上顿时跳起指头般粗的鞭痕儿;落在骡马的脖颈上,鬃毛如用刀剪一般,纷纷扬扬。故而扶犁匠的拖鞭经常背在肩头上,不轻易放实鞭,只要用鞭把儿轻轻敲敲犁把儿,犋上的牲口就乖乖地卖劲,听使唤。其二曰“虚鞭”,它只有如雷的响声而不着牲口的皮肉,此鞭也叫响鞭。临淄的扶犁匠们有经常放响鞭的习惯,那是他们自我陶醉的一种乐趣罢了,并非为了打牲口,故家乡有“扶犁匠打响鞭——自图快活”的歇后语。踏耙更有趣。在刚耕过的面窝儿似的土地上,扶犁匠站在耙的踏板上,一手持住牲口缰绳,一手挥动着摇鞭,随着双脚交替起落,使耙均匀地摆动拖行。耙像一把巨型的梳子,划出几十条波浪线……耙过的地块犹如一架琴弦颤抖的巨型古琴……踏着耙在松软的地面上滑行,既有坐荡椅的飘荡感,又有坐雪橇的滑行感。耙坷垃地,耙上下颠簸,比坐花轿还惬意呢!
晚归时,幻变、神奇的犁铧更有趣。每当日薄西山,晚霞映天。老牛摔着尾巴慢悠悠地拉着拖车归来。扶犁匠轻哼着梆子腔,高了兴左右开弓,放几声响鞭,惊得停树待宿的鸟雀扑愣愣乱飞,引得光腚孩子雀跃拍手……拖车上那面擦拭得油光可鉴的犁铧上,映物照人,变幻莫测,它简直是一面小型的哈哈镜:它能把西山上高大的柏树照成矮矮的狼尾巴蒿;它能把山上低矮的小庙照成一把硕长的出鞘宝剑;它能把晚归的绵羊照成高大的骆驼;它能把清瘦的老扶犁匠照成笑眯眯的弭勒佛。光腚孩子们当看到他们的苹果脸照成“二指脸”小鬼时,闹罢恶作剧后,在路旁二指厚的簿土里打“旁连”、竖“直立”……
搭犋耕地虽说能自寻些田园乐趣,但更多的则是劳累和烦恼。用大骡大马搭犋的毕竟是少数,大多数农户是老牛、瘦驴搭犋。笔者十六岁时就曾当过老牛瘦驴犋的小扶犁匠。老牛在狭窄而暄松的墒沟里打别腿; 瘦驴的腿像抽筋,蹄子抬得老高落不下,其乏力之状不言而喻。笔者摔的鞭既不响又无力度,打老牛一鞭,腚一斜,打瘦驴一鞭,腰一弓,把犁拉得东倒西歪,笔者只得像醉汉逛街似的“救犁”,耕的地像长虫吃了蛤蟆。一天下来嗓子喊哑了,浑身像散了架,躺在土炕上“翻饼”……然而四驴子犋的扶犁匠却是最生气、最烦恼的差事,四个毛驴搭一犋,像一串乱蹦哒的蚂蚱,叫驴们拉犁虽无力而性欲却十分亢奋,发起性来,大叫不止,东咬一口,西踢一蹄。草驴们吓得不是畏缩不前,就是奋力挣脱。扶犁匠既使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。若狠打几鞭,打着的拉一膀,打不着的松一套,不是这个脱了“杆儿”,就是那具拌了腿,乱成一窝蜂似的。真是应了“四驴子犋活生气”的俗语。要说最苦最累莫过于冒雨踏耙,搭犋是几家畜力和农具的组合,确实不易,小风小雨,谁敢轻易歇犋,再加上“只耕不耙”是大忌,俗话“耕地不耙,炉碴,瓦垡”,因此不管耕了多少地必须赶在雨前耙完。当暴风雨初来时,还能拖泥条踏耙。待到暴雨倾盆而降时,就只能“畜拔响蹄”,人“跟耙踩藕”了。人畜成了落汤鸡,其苦累之状可想而知。
扶犁匠们尽管至苦至累,反而煅红了他们那颗爱犁、护犁的执著、赤诚的红心。俗说扶犁匠有两大怪:“鞋底完好帮早坏,蓑衣不披给犁盖”。凡是耕地回头、间歇,晚归“上拖”时,扶犁匠总是习惯地用右手提起犁,用左脚的鞋帮将犁铧擦拭几下,故而鞋帮先破。扶犁匠的蓑衣,即使雨下得再大自己也不披,宁愿自己挨淋,也要将犁铧盖个严,以防焐犁。扶犁匠们的敬业之心可见一斑。
春耕之后,为了保墒,间或再耙几次,就等雨后春播了。
选自王毅《临淄古今民俗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