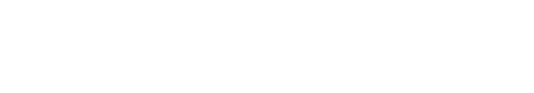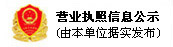齐都临淄稷下学宫,是战国时代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和诸子百家荟萃之地,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,其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。
所谓“王道”,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,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;所谓 “霸道”,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,来称霸诸侯,武力征服天下。战国时期,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,中国走向统一的大趋势已露端倪。怎样实现由乱到治、由分裂到统一?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?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。
儒家大师孟子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。他认为,“以力假仁者霸”,“以德行仁者王”。他反对霸道,认为“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”;主张王道,因为这是“以德服人,中心悦而诚服也”。
荀子虽然崇尚王道,但面对当时盛行霸道的现实和对齐文化的吸收,也谈霸道。他主张在王霸并容的前提下,以王道为本。
管仲学派主张王霸并举,是实行王道还是实行霸道,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定,即“霸王者有时”,“以备待时,以时兴事”。他们认为,“强国众,合强以攻弱,以图霸;强国少,合小以攻大,以图王。”还说:“战国众,后举可以霸;战国少,先举可以王。”可见,管仲学派的王霸学说更适合当时的时势,更具有现实性。
二、义利之辩
义利之辩是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的一个很普遍的辩题。
孟子继承了孔子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的思想,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,认为追求利必然损害义,为了保拿义,要“舍生而取义”,“二者不可兼得”。
荀子把义利关系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,他认为人们对利的追求具有合理性,是人的本性,但认为这种追求要保持一定的度,不能放纵。放纵逐利,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。荀子认为,要用礼义制约人们的物质欲望,教育人们“先义而后利者荣,先利而后义者辱”,反对“唯利之求”。这样做了,国家就会平治,反之,则会出现乱世,即所谓 “义胜利者为治世,利克义者为乱世。”
管仲学派对义利关系的看法是义利并重。他们认为:“爱利足以亲之,明智礼足以教之”。讲礼义教化,不忘记物质利益的激励功能;讲物质利益,也不忘记礼义教化的引导作用。二者相得益彰,相辅相成。
三、天人之辩
天人之辩,首先要回答天是什么,然后再回答天与人的关系如何。稷下各学派围绕天与人进行了交流与争鸣。
孟子认为,天是人事的最高主宰,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。在孟子看来,人民的降生、事业的成败、帝王的权位、天下的治乱,都是天的指令。实际上,孟子将天看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的实体。由此,他沿着"尽心、知性、知天"的思维模式和认识路线,建构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。
荀子认为,天就是自然界,其运行变化具有规律性,这种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即 “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”荀子还认为,人是天下最珍贵的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,并且不是一般的部分,而是特殊的一部分。荀子基于对天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,提出了“明于天人之分”、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光辉思想。
管仲学派对天人之辩的回答也是唯物主义的,而且更具有现实性,比如《管子·度地》从具体的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认识天人关系,将能根除水、旱、虫等五种灾害说成是人能主宰自然界。
四、人性善恶之辩
稷下学宫中,关于人性的善恶之辩,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看法。
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,因为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和生来就具有仁、义、礼、智四种善端。至于人做了不善的事,不是因为其本性不善,是由于他自己不把握自己,被形势左右所致。
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,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。人性的善端,不是生而就有的,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。
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。荀子认为在人性中,最能支配人类生活的是人的好利恶害之情,而好利恶害发展的结果,必然产生尔虞我诈、巧取豪夺等不道德的行为,所以说人性是恶的。他同时认为,这种恶的人性,经过后天的学习教育,注重对"人性"的改造,就可以做出善的行为。
五、世界本原之辩
管仲学派最早把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,认为世界万物产生于气,最终又复归于气,并进而提出了唯物主义的“精气说”。稷下先生宋钘、尹文认为“精气”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,“气”就是“道”,是客观的存在。
管仲学派还提出了水是世界万物本原的学说。《水地》篇说:“水者何也?万物之本原也,诸生之宗室也。”
稷下道家季真提出“莫为”说,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是自我运动的结果,否定“天命”的主宰作用。
稷下道家接子则提出“或使”说,认为“道”是天地万物的本原、始基。
荀子认为,“天地”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,“天地合而万物生,阴阳接而变化起”。
阴阳家邹衍认为,天、地并不是从来就有的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,它们各有自己生成和发展的自然历史,在时间上是有始有终。但是,在天地产生之前还有一个不可考之原,还有一个天地未分的原始状态,也就是说,整个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。
六、名实之辩
“名实之辩”是讨论概念(名)同它所代表的事物(实)之间有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。
稷下先生宋钘、尹文主张“名当”,认为“名不得过实,实不得延名”,反对“刑(形)名异充”,坚持先名后实、名宜符实的名实观。
稷下学者儿说提出“白马非马”的著名论题,其后,公孙龙在《白马论》中对这一论题进行了充分的阐发,他将马的形与色析而为二,只强调了个别与一般的差别、对立和排斥,否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,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诡辩论。
稷下学者田巴以辩论“离坚白、合同异”而闻名于稷下。同公孙龙一样,“离坚白”将通过触觉感知的坚硬石质同通过视觉感知的白色外表分离开来,互不联系,否定了大脑的综合作用,否定了人的认识的能动性。